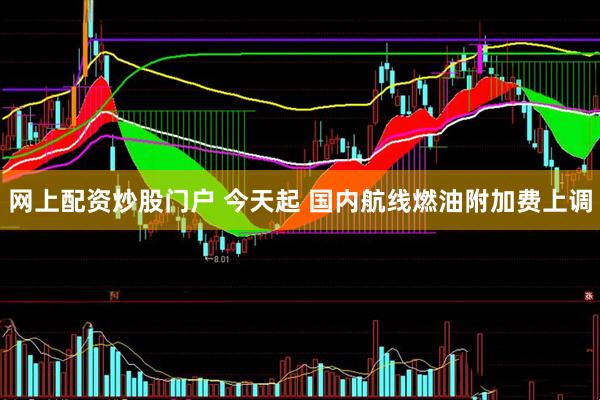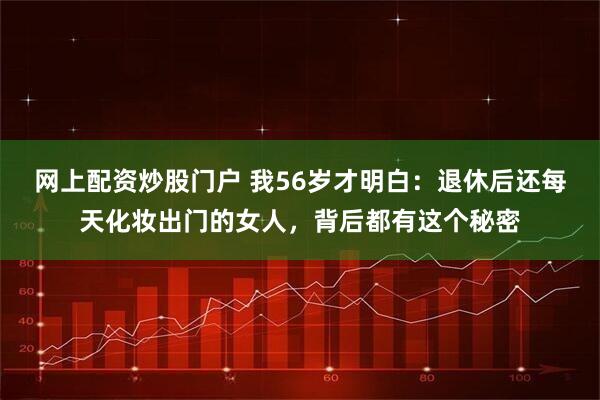本文转自:文汇报网上配资炒股门户
陆千一
陆千一(第二排左一)和学生们在一起
陆千一
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陆千一,曾在西北地区一所职业院校担任语文教师,她的新作《我是职校生》穿透偏见,让占同阶段教育总数近40%的人群发出自己的声音;天津的民间入殓师韩云的新作《花落了》通过数个亲历的故事,呈现了中国社会四十年来生死观念的演变,是一场关乎记忆与告别的生命教育;生于新疆、长于新疆的乌图禾在四十岁时出版了首部小说集《大马戏》,把乌鲁木齐旧时的日常和传奇,讲述给今天的人们听……他们是烟火人间的观察者,也是灿烂生命的记录者,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打开了世界,让读者看到“场景里的中国”。 ——编者
六年级是我孟母三迁式的求学道路上最快乐的一年。我转入名牌小学后的两年,我爸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祛魅,他发现学校好不好和孩子高不高兴是两回事儿,请不请老师吃饭和孩子自不自在更是两回事儿。第二次转学,我爸痛定思痛,让我在家门口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匆匆入学了。
学校像极了黑柳彻子作品《窗边的小豆豆》中的“破学校”巴学园,只有一栋孤单的、墙皮斑驳的教学楼——要知道名牌小学甚至有一栋单独的厕所——和对面的中学共用坑洼不平的土操场。整个校园隐于一个脏乱的菜市场内,上课时常能听到楼下的叫卖声,学生便探头探脑,和楼下的小贩打招呼。我关于这一年的记忆,也漂浮着菜叶被踩碎、流出汁水的清凉味道。然而就是这一年奠定了我性格甚至生命追求的底色,我想这也正是小学教育的意义所在吧。
很多年后,当我尝试用后来读过的书、学过的知识,重新理解这段经历的存在时,我仍不得不把一切归因于我们的老师,以及她给予我们的、朴素的平等。
我的两次转学都与老师有关。在第一所小学,那时还不到三年级吧,老师让当班长的我掌掴迟到的同学。直到现在,我仍记得我和那个高大的男生面面相觑的尴尬,老师在身后威逼,最后我不得不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脸便落荒而逃。这件事的心理阴影让我第一次隐约产生了所谓教育就是管理的意识,也成了我第一次转学的导火索——当然,我想这件事对那位同学的阴影应该远超于我,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向他道歉。
新学校是本地排得上号的名牌小学,学生家长多是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,老师毫不掩饰,她曾在课堂上直言,一个对我很友善、热情开朗的男生是“山上来的”——大概就在这个阶段,我心里有了一个后来读到的“反学校文化”的影子,因为随着时间推移,我发现班里所谓的差学生大多是“被认为”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。
——关于这位老师,能讲的故事实在太多。有一次,她询问我们几个班干部,要不要惩罚一个做错事的同学。此时我长大几岁,当场说不,结果全班被她留下,听她痛骂我。家里知道后表示忍无可忍,第二天我就没去上学了。
小学高年级,随着心智逐渐成熟,我已经开始对学校的正式领域产生怀疑。然而转入“巴学园”后,我却再也没遇到过这种“分而治之”的事。当然,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权力理论,只感到班里的氛围出奇地好。无论什么类型的学生,在班上都能交到朋友;同理,和什么类型的学生交朋友,都不会受限。成绩好且听话、成绩好但不听话、成绩差但听话、成绩差且不听话,学校文化与反学校文化奇妙地融为一体。至于因长相、成绩或性格被霸凌,更是没有的事。
我们的老师姓彭,是个快退休的女老师,我们是她的最后一届学生。她一个人租住在学校附近,丈夫和女儿都在外地工作。放学后时间空余,她便把家长无暇接送的学生留在教室写作业,偶尔甚至带回家里吃饭。到了六年级,班上总有些和校外联系紧密、视我们如小屁孩的“班霸”,他们说起她,仍尊称一声“老师”。
事实上我和这位彭老师的关系并不亲密。一方面毕竟相处时间不长,另一方面我情感内敛,不善表达。然而在这个班里,我不需与她亲密就能感到安全。因为她公正地对待所有学生,这是一种比受到偏袒更持久的安心。难以避免地,她往往和性格活络的同学接触最多。但从事实上看,无人受偏袒,无人被冷落。于是时间久了,老师和同学的接触,就变成了一种无涉权力的正常相处。即便像我,这个和她话都没说过几句的插班生,一次突然肚子疼,也是由她,一个体弱多病的、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亲自背到医院。
很多年过去了,我从没想到自己有机会写作一部与教育相关的作品,并为之撰写创作谈。思考良久,我决定用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这部作品,或者说我某个人生时期的总结。我当时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,大多像我一样个性分明。即便兴趣千差万别,成绩有好有坏,也不影响我们成为朋友。我们一同上补习班,也一同去电玩城或美食街。好学生、坏学生、书呆子、班霸,没有一张标签能概括我,没有一张标签能概括我们。后来我们当然被“分流”到城市的不同角落,按照既定标准,被输送到社会的不同位置。学校教育似乎是一场漫长的异化,个体的生命经验仿佛是最不重要的事。正因如此,那一年始终是在时刻提醒身份与壁垒的学校教育中,给我短暂的自由喘息。
如今,我告别学生身份将近五年,离开教师岗位也一年有余。在这个主题下,最适合我的表达身份不再是参与者,而是一个随时可能与教育发生交集的普通个体。在某种程度上,我的经历或个人化思考也代表了部分亲历者的真实感受。学校教育看似只占据了人生的小小片断,然而这一强大的集体仪式,却用潜移默化的社会常识框定了我们的未来。这部职校生口述史完成于一年前,之所以选择口述史写作,我在序言里这样写道:“我试图对于一群人进行文学创作而非理论研究,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目标下,我没有资格用主体的单一视角诠释她或他所属于某一群体。在我工整的文字之下,他们只会成为一个人物符号,然而他们的人生远比一篇故事、一个结论中的符号更丰富、更具体。”事实上,在写下这句话时,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现实:“具体的人”并不孤立存在,而是跻身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议题下。他们是我的小学同学和彭老师,也是我在职校任教时的学生们。他们的存在比我想象中更真实,也比我想象中更艰难。
当然,相比普通教育,职业教育暗藏着更大的神伤。一个出身农村、在职校求学、个性鲜明、对未来抱有憧憬的普通孩子的生命经验也值得我们珍视。制度提供的是规则、框架和目标,但真正让一个孩子发生改变的,不是制度本身,而是具体的人或关系。如果这部作品能够传达出哪怕一丁点儿抽象概念、理性语言之外的力量,我想它存在的价值就实现了。不过对我来说,这部作品能够收获同学们的喜欢已经是最大的价值。他们为自己的故事变成铅字而兴奋,纷纷发抖音、发朋友圈,有一个甚至扬言要去放炮——虽然后来连媒体采访也没敢尝试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评论来实现自我认可。
前段时间网上配资炒股门户,我在上海见到了两个工作了的学生。一个跑车,一个做电话销售。做销售的那个晚上十点下班,我们在一幢昏暗的写字楼下等到十点半,才看到大厅亮灯,一群年轻人鱼贯而出。据他说,因为这个月业绩不好,公司大会小会不断,他也常常被点名批评。说着象征性地丧气了几秒,便恢复了活跃。将近12点,我们在几十公里外找到了一条还在营业的美食街。城市的边角没有漂亮招牌,然而街上同样热闹,店铺多半打烊,人却来往不止,好像白日看不见的光影。我们一边吃饭,一边聊工作、生活、新闻、娱乐八卦。在上海的数日甚至当天下午,我都疲于应付不同的约会,但只有在这顿饭上,我感受到了强烈地被尊重。相比上学时,我们似乎有了更多话题,然而我们仍是如此不同。一个学生讲起正在组织的租车生意,我听得一头雾水;我说起和作者沟通的写作细节,他们似乎懵懵懂懂。有时候我把他们当小孩,有时候他们又觉得我幼稚——像“温室里的花朵”,如他们所言。但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一点心照不宣,接着求同存异地交流并成为朋友。人可以作为一个人,而不是某个观念、身份或行为的碎片,受到理解和尊重。这是在这段口述写作,或者说共同成长的过程中,他们教会我的。
通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网上配资炒股门户 在澳洲玩暖暖国服,犹豫要不要抽满
- 下一篇:没有了